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日渐为四川省学术界的各个考古机构所认识。198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建立了工作站,负责遗址的保护、发掘和研究工作,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与蜀王故都的关系逐渐有了深入而明晰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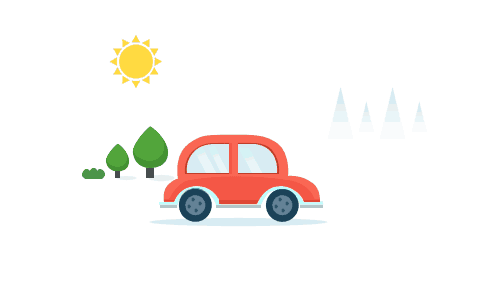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1929年出土后存放在燕家院内土砖墙侧的大石璧
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倔,在蜀王故都的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首先是探明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达12平方公里。分布最集中、堆积最丰富的地点,有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其次,找到了相当于夏、商、周时期的房屋基址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再次,发掘出土大量陶器、玉石器。尤其是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立像、青铜面像、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龙、青铜蛇、青铜夔、青铜凤、青铜鸡,以及金杖、金面罩、象牙、海贝等稀世珍品上千件。另一重大发现,便是三星堆城墙的发现与确认(《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分载《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为蜀王故都的重见天日提供了铁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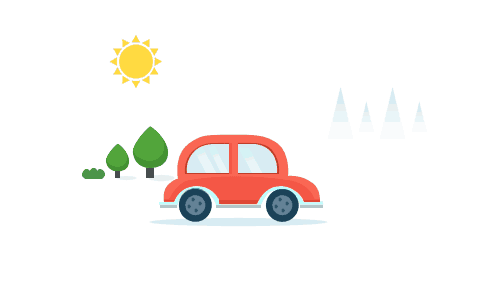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发现处
1988年以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的土埂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掘工作,获得重大成果。试掘探明,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在主城墙局部,使用土坯砖,这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调查和勘测结果表明,被城墙所围的城圈范围,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总面积3.6平方公里,面积超过郑州商城。城墙无转角,不封闭,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文化堆积层较丰富、集中。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出土的两个大型祭祀坑,都位于这一中轴线上,说明这个区域是三星堆古蜀国都城最重要的宫殿区。在城墙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东城墙和南城墙内侧,发现城墙夯土压在三星堆一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三星堆二期(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期)偏晚文化层所叠压。从地层分析,三星堆城墙的时代相当于早商时期(陈德安、罗亚平:《蜀国早期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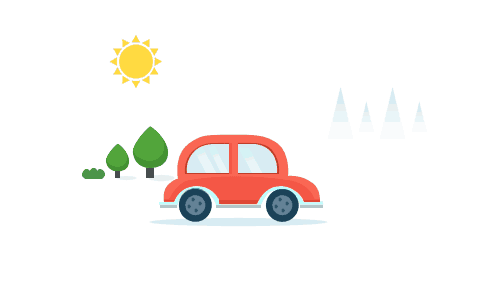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古城东城墙发掘现场
这次调查、勘测和试掘,确认了三星堆城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古蜀国的都城,使数十年以来学者们对蜀王故都的探索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整个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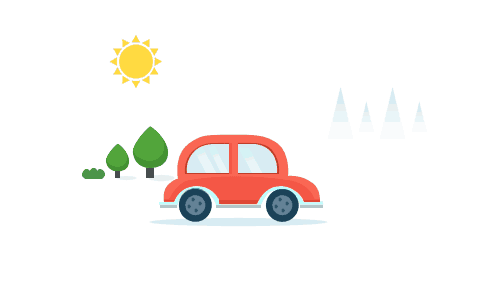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古城西城墙发掘现场
关于蜀王故都,历史文献记载显得过分简略了。三代蜀王的故都所在,蚕丛、柏濩两代完全没有什么材料传世,至于鱼凫王的故都,文献记载也是浑浑噩噩,似乎所在皆有。《蜀王本纪》说:
鱼凫田于湔山(按:今都江堰市境内),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华阳国志·蜀志》也说:
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解释: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州国》也说:
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既然古蜀人在今都江堰市境内的湔山建立了鱼凫王庙,那么那里便似乎就是鱼凫王的故都所在了。
可是,持不同见解者大有人在。唐人卢求的《成都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6引)、宋人罗泌的《路史·前纪》都不以为然。这两部书均认为:
鱼凫治导江。
“导江”在今都江堰市南,与湔山并不在一个地点。不过,从大范围来看,两地都在今都江堰市境内,差距不太大。
宋人孙寿的说法,差距就很大了。他在《观古鱼凫城诗》的自注中写道:
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
清嘉庆《温江县志》充分肯定这一说法:
(鱼凫王城)在县北十里。俗称古城埂。
这几种说法,孰是孰非,自古以来,人们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辨析。
所幸的是,科学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古蜀王国秘密线索的钥匙。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大批文化遗物的出土,大量文化遗迹的披露,尤其是古老城墙的发现,证实了上述古籍所载蜀王故都并非虚幻。因为,一座金碧辉煌的蜀王故都,已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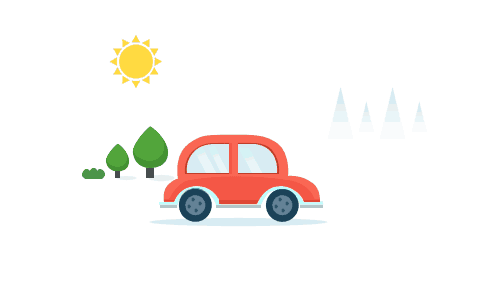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古城墙遗址
三星堆文明的再发现,举世瞩目。但是,要确切证实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故都,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工作。
三星堆古城址的现存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占地面积,即使在当时(早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城墙体的高大、坚厚,反映出可供支配、征发和役使的劳动力资源相当充足,进而可知居住在城内的统治者必然高高在上,统治着数量庞大的人口,控制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城圈的广阔,其实质是意味着城圈以内复杂社会的形成,表明其中的生活方式已经截然不同于史前的乡村,城圈内部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的控制系统和运作机制,都已远远超出史前酋邦的水平。再结合对为数众多的直接生产者和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各种艺人)的有效统治以及对自然资源、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高度控制来看,一个具有集权性质的政府组织显然已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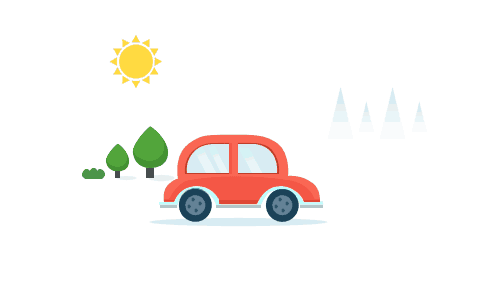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出土大型建筑遗址
在三星堆古城以内已经发掘清理的房屋密集的生活区中,出土了大量陶质酒器、食器和玩物。发掘清理的房屋遗迹,既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权贵们居住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还发现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更发现了面积达800平方米以上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几种房舍的区别,揭示出其间深刻的阶级分化。在生活区内,发现了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出土了大量青铜艺术品和工艺陶塑制品、动物、乐器等,还出土大批玉石礼器和雕花漆木器,出土双手反缚、跽坐的石雕奴隶像,相反却缺乏农业生产工具(林向:《蜀酒探原》,《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表明这些区域是贵族统治者们的居宅。这就与其他仅出土大量生产工具、成品半成品和手工作坊遗迹的区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展示出建筑群依照房舍主人身份的贵贱高低进行分区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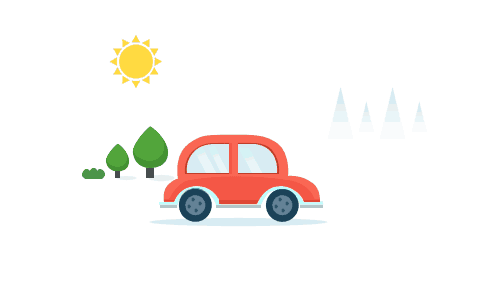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青关山大型建筑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海贝、象牙和玉石礼器,无一不是权势与财富的代表和象征。它们显然绝对属于城内的核心统治集团所拥有。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遗址内发掘出的4座墓葬,基本上谈不上有随葬品,更不用说有什么金银财宝。这当中的区别,透露出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严酷的阶级剥削的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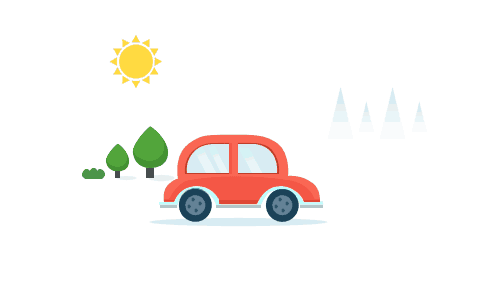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公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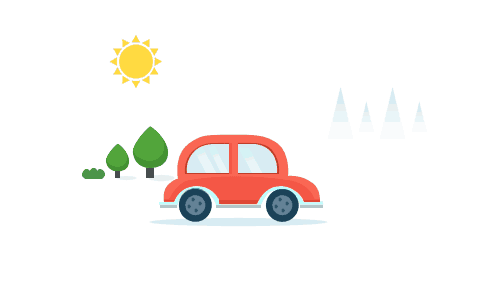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高耸的城墙,城墙外围深陷的壕沟,是阶级冲突加剧的象征。遗址内一些出土陶器上的早期文字符号(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四川文物》“三星堆研究专辑”,1989年;段渝:《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成都文物》1991第3期,《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野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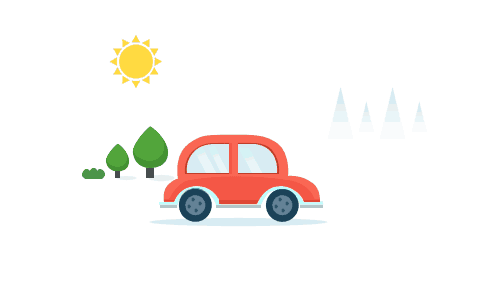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的文字符号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十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相同。这些遗址群,既与三星堆古城土壤相连,又被三星堆高大的城墙隔开。它们毫无疑问是三星堆古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的乡村群落。古城内的粮食、生活用品和一应物品,多来源于此,取之于此。这正是古代城乡连续体业已形成的最显著实例。三星堆古城,显然首先就是作为这片广阔乡村的对立物,从中生长、发展起来,并凌驾在它们之上,对它们实施直接统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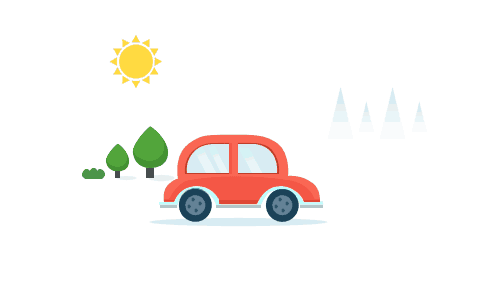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成、渝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分布示意图
古蜀地区各种生产资源、社会财富和富于战略意义及宗教神权巨大权威的自然资源,向着三星堆古城的单向性流动和高度汇聚,表现出三星堆古城对整个古蜀文化区的高度凝聚力、向心力和高度的社会控制;而古蜀文化区各地的青铜兵器等军事装备,又是从三星堆古城呈反向性地流向各个次级邑聚、边缘地区和军事据点,表现出三星堆古城对整个蜀文化中专职暴力机构和军队的强有力控制与指挥。这两种现象确凿无疑地说明,在古蜀王国的巨大社会控制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调控枢纽,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其核心是王权与神权。
以上所有的因素,无不揭示出人口集中的大规模化,人口结构中非直接生产者的大量产生,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商业关系的广泛建立和远程贸易的产生,社会分层的复杂化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大型居住区与贫民窟的对立,巨型宗教礼仪中心的建成,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专业艺人队伍的存在以及神权与王权的强化和统治机器的专职化、制度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整合起来看,正是业已形成为一座早期城市的最主要标志,构成一幅城市文明的清晰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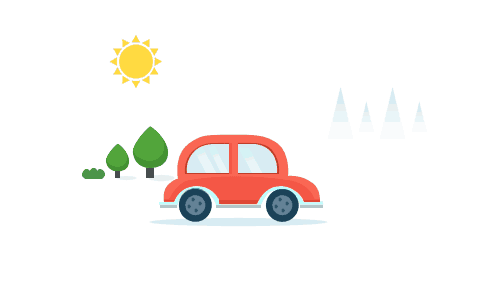
三星堆古城北城墙下的疑似建筑基址
即令从经济进步的角度来认识,三星堆古城所拥有的大规模青铜器生产、玉石器生产和金器制作以及昌盛的酿酒业、建筑业等,都无不显示出远远高于史前村落的经济发展程度。因此,作为城市化机制的核心,三星堆遗址也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它作为多种产业生长点和地区的增长中心的特点。因此毫无疑问,三星堆应是一座典型的古代中心城市,即都市,也是古蜀文明的高级中心之所在、权力中心之所在,即古蜀王国的都城。
